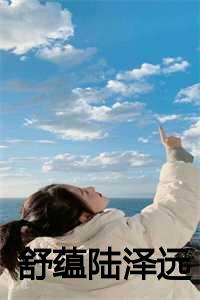- 作品分类
作品简介
扫完墓从寺庙出来,周夫人的车下山了,那辆红旗L9还在。车窗敞开,风雪刮进后座,周宴晖在一片浓白的雾气里,望向她,“我送你回学校。”“出租呢?”她给了两百块钱,让司机等一会儿。...
精彩章节试读
“太贵了,不适合在学校用。”
他手肘支着车窗,闭目养神,“丢垃圾桶。”
杜若顿时无言以对。
自从父亲的财产充公,家里又断了收入来源,她太知道没钱的窘迫了,二十万的包哪里舍得扔掉。
周宴晖更知道她舍不得。
杜若没理他。
再行驶过一个路口,快到周宅了,周宴晖忽然问,“你跳什么舞种。”
“古典舞。”
他侧过头,打量她的细腰和手臂,娇软纤长,却有柔韧度和力量,是练舞蹈的身材。
周宴晖没有上流圈的陋习,但也和上流圈交际。
那群人偏爱舞蹈生,有十几年的童子功是最好的,柔软得可以翻来覆去各种姿势。
“毕业典礼你表演吗。”
杜若抿唇,“那天你来吗?”
“有时间会来。”
周宴晖一贯是这副样子。
不明确的暧昧,不挑明的甜头。
留下回味,以及抽身的余地。
车拐弯开进小区,周宅是1号院,一套四百平米的徽派合院,灰白色砖瓦,入户的影壁墙挂着大红色中国福字结,气派恢宏。
司机停好车,拿起扫帚扫干净车门外的雪,周宴晖才下去。
皮鞋油光水滑,不沾一丝雪和泥。
周宴晖下班住市中心的大平层,六日必须回周宅,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饭,看新闻,向周淮康汇报工作。
是周老太爷那辈立下的规矩。
院子里的柿子树染着白霜,周宴晖经过树下,抬手摘了一颗大的给杜若。
“柿子熟了。”
她一摸,带冰渣的。
生理期不能吃凉。
杜若摇头。
他握在手里,“不爱吃了?”
“过两天再吃。”
杜若也不晓得他懂不懂,她不可能怀孕的。
周宴晖迈上台阶,打开红木大门,吩咐迎接的保姆,“煮梨汤,杜若喉咙不舒服。”
她瞬间想起周宴晖那晚躺在浴缸里,摁住她后脑勺往下压的一幕。
腹肌紧绷,硬邦邦的,硌得她嘴唇发麻。
杜若半点经验也没有,疼得周宴晖额头冒汗,他仍旧没松开,嘶哑着喊她名字,逼她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