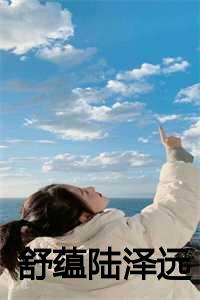- 作品分类
春风吹不尽免费小说鹿一白,周怀幸全章节阅读
导演来敲门的时候,鹿一白就被周怀幸抵在门后面。
化妆间是剧组临时搭建的,门板薄而不隔音,敲门声的震动透过门传到她的后背,让她猛地缩紧了身体。
周怀幸呼吸一重,惩戒似的拍了拍她的臀。
“放松。”
男人一双眼狭长,低头看她时,多情又薄情。
鹿一白双腿悬空,牢牢地攀着他,外面敲门声不断,她还能睁着一双雾雨朦胧的眼去勾引人:“我放松了,周总还怎么爽?”
大概是怕外面的人听到,她贴着他的耳朵,声音与呼吸一同落到耳边。
周怀幸的呼吸就更重了,他抬手捏住了鹿一白的下巴,低头去咬她的唇,话语含糊在唇齿间:“你确定?”
与之一起的,还有男人突然加重的动作。
门外敲门声顿了一顿,导演试探性的声音隔着门传过来:“鹿小姐,您在忙吗?小周总还在不在?”
鹿一白半个字都说不出来,眼前人还不肯放过她,呼吸带着点热意:“回答他。”
周怀幸是故意的,鹿一白心知肚明,但她理亏在先,只能伏低做小:“我错了,帮我。”
她后背抵着门,菟丝花一样的攀着他,眼里春波横生。
周怀幸终于大发慈悲,冲着外面说了一句:“在忙,有事?”
他的声音清冷淡漠,带着点不耐烦,导演瞬间明白:“打扰您了,没什么大事,听说您过来,我特意订了宴席,稍后能赏光吗?”
周怀幸拒绝的话就在嘴边,又转了一转,隔着门问导演:“时宴去吗?”
鹿一白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幸好导演不傻,赔笑着回他:“时宴下午有个活动,请假了,明天上午才来,要不下次再请他?”
就刚在片场那一出,他不要命了才让两个阎王见面呢。
鹿一白顿时松了口气,周怀幸意兴阑珊:“我还有事,下次再吃。”
门板微微震颤,导演看了一眼,话里带着点暧昧:“小周总先忙,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鹿一白在心里骂了一句,听得人声远去,还不等放松,周怀幸一把抱起了她,放在了化妆台上:“咱们继续算账。”
这人说到做到,等到算完账,已经是一个小时后了。
周怀幸靠着化妆台抽烟,鹿一白在烟圈氤氲中看他。
他衣冠楚楚,她一身狼狈。
“看什么?”
周怀幸火气消了大半,逗弄似的捏了捏她的脸,鹿一白撒娇似的点了点脖颈:“我下午还有一场戏呢,小周总倒是下得去手。”
她皮肤娇,一片红痕铺开,暧昧又色情,明眼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周怀幸眼眸微深,语气轻佻:“不打个标记,有些人以为谁的东西都能觊觎了?”
这人话里又带上了火,鹿一白讨好似的贴过去,在心里骂了一句害她的疯子。
疯子就是时宴,是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业界翘楚,戏是真好,一个眼神就把她带入了人物。
剧本是破镜重圆,那一场她被发现真相的男主强吻,本来吻戏是该借位的,可入戏情动时,时宴把她摁在了墙上,直接吻了上去。
正好被前来探班的周怀幸看了个清清楚楚。
周怀幸这人霸道专横,洁癖又龟毛,他把鹿一白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当然不允许自己的东西被沾染。
周怀幸拉着她在化妆间里泄了一回火,他倒是神清气爽了,鹿一白却是浑身疼,还得忍着疼给大少爷顺毛。
“那是拍戏,又不是真吻,我也及时躲开了。”
她乖觉的不继续这个话题,又语气乖巧的撒娇:“况且,剧组谁不知道,我是你的人呀?”
鹿一白这话是实情,她在周怀幸身边六年了,圈里人都知道她金主是极昼的太子爷,以前拍戏也都好好的,结果这次遇到了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宴。
说实话,那场戏她拍的还挺过瘾,但这么作死的话鹿一白是不敢说的,只能再三保证不会有下一次,又冲着周怀幸撒娇说疼。
眼前人跟狐狸精似的,周怀幸脸色好看多了,捏了捏她的脸,语气散漫,带着警告:“记着自己的身份。”
鹿一白知道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心里松了一口气,面上乖巧的答应,还不忘勾引他:“要不小周总今晚留下来,我再好好儿记一记?”
周怀幸随手系上衬衣扣子,淡淡道:“不了,还有正事儿。”
现在她浑身酸软,他倒是神清气爽,鹿一白心知肚明,这人在自己这儿的正事儿显然是办完了,虽然知道他来找自己只有这个,心里还是有点儿酸。
鹿一白忍着那点酸楚,面上还带着笑:“行吧。”
她说话时站起身来,贴近了周怀幸。
女人纤细的手指抓住了他的领带,一圈一圈的缠绕在手上,而后绕过了他的脖颈。
周怀幸低头看她,见她眼眸中水光潋滟,低声问:“想做什么?”
鹿一白眨了眨眼,带着点不谙世事的纯情:“领带歪了。”
她的唇有点肿,是被肆虐过后的红润。
周怀幸的眼眸微深,拍了拍她的脸:“安分点。”
这人倒打一耙,鹿一白咬唇看他:“小周总这话我可不明白,我还不够安分吗?”
周怀幸最喜欢她的一双眼睛,像鹿一样无辜又干净。
六年前他生日那天去赴酒宴,鹿一白一身酒气、狼狈的撞到他怀里,当时也是睁着这么一双眼。
纵然他知道她的目的不纯,可还是将人收下了。一个金丝雀而已,目的再不纯,也翻不出他的手掌心。
所以眼下他只是摩梭了一下她的脸颊,声音里带点儿逗弄似的漫不经心:“刚才没喂饱你?”
- 司嫣(穿成四个蛇仔仔的娘亲)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司嫣免费最新章节列表(穿成四个蛇仔仔的娘亲) 2024-05-29
- 全文浏览冬至缚情(姜雪笙谢渊)_冬至缚情(姜雪笙谢渊)全文结局 2024-05-28
- 薛欣如陆森年后续全文(薛欣如陆森年后续)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陆森年薛欣如全文在线完整版阅读 2024-05-28
- 完结文我养的小白脸总想上位(上)最新章节列表_完结文我养的小白脸总想上位(上)全文免费阅读(秦伟天,许墨沉,秦宅) 2024-05-28
- 全文浏览我养的小白脸总想上位(上)(秦伟天,许墨沉,秦宅)_我养的小白脸总想上位(上)(秦伟天,许墨沉,秦宅)全文结局 2024-05-28
- 传闻命绝之人向健康的人磕头即可向活人借寿最新章节列表_传闻命绝之人向健康的人磕头即可向活人借寿全文免费阅读(小妍婆婆) 2024-05-27
- 热吻玫瑰会上瘾(热吻玫瑰会上瘾)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娆顾琛最新章节列表(热吻玫瑰会上瘾) 2024-05-27
- 热吻玫瑰会上瘾(热吻玫瑰会上瘾)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娆顾琛列表(热吻玫瑰会上瘾) 2024-05-27
- 热吻玫瑰会上瘾(温娆顾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热吻玫瑰会上瘾)热吻玫瑰会上瘾最新章节列表(温娆顾琛) 2024-05-27
- 温娆顾琛(温娆顾琛)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热吻玫瑰会上瘾大结局)温娆顾琛最新章节列表(温娆顾琛) 2024-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