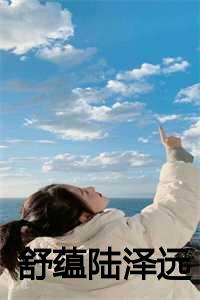- 作品分类
全章节小说绝望木偶人by苏清河涂灵莹阅读
我把他单独叫出来,然后问他是不是叫范正豪。
他说是。
我说我把你查清楚了,你家里有钱,留了案底也不怕。你当初书都没读完,娶了老婆也不去上班,一直花天酒地,你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只玩从来不干正事,靠爸妈的钱过日子。
可是我老婆呢?
我老婆喜欢炖汤送到我们交警队,每次都把旧衣服收拾好送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每年冬天都去探望孤寡老人送棉被粮油。哪怕她去世了,也因为生前签过器官捐献,帮助了那些急需活下去的人们。
我说你他妈真是个人渣啊,和我老婆比起来,你活着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低着头不敢讲话,应该是还记得我当初怎么打他的。
我没忍住哭了,我擦着眼泪,说你活着到底有什么用?我老婆那么好的人,最后就换来了你的一场缓刑。你要是活得有那么一丁点意义,我都不会沦落到这么心痛。
他就不停给我道歉,说他真的知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让我原谅他。
我也不想和他多说什么,我就说我老婆用命换来了你的改过,你以后真的要好好做人,你身上背着她的命。
……
我看向旁边这位女孩,虽然她梨花带泪,但是不难认出,她就是图片里的那位记者!
我走到她身边蹲下,说:「本篇报道记者……涂灵莹是吗?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把罪犯写出浪漫色彩的记者,每次看到这类报道,我只会觉得恶心。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在朋友眼里是老实人,查询罪犯到底是因为什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来,你看,你仔细看。」
我指着那在地上气喘吁吁的朱程亨,轻声说:「你看他哪儿忠厚?你看他哪儿老实?罪就是罪,恶就是恶,世界上童年悲惨少年辛苦的人多了去了,每个人都是很辛苦地活着,怎么这反而成为犯罪的浪漫背景了呢?来,你现在看看自己写出来的文字,再仔细看看他的脸。」
涂灵莹眼泪不断落下,我给她松了绑,她立即擦着眼泪,捂住了自己的嘴,失声痛哭。
我站起身,来到了朱程亨的身边,仔细搜了搜他的身,搜出了胶带、注射器,还有刚才被我打落的尖刀。
我仔细看着这份报道。
八年前,他绑了一位妇女,将她手脚束缚跪趴在地上,用注射器做威胁,强迫她服从自己的命令。
我一脚踹在他的头上,冷声说:「跪着,趴着。」
朱程亨有点不想做,我便拿起注射器,对准了他的眼睛。
我没有留手,注射器的枕头直接顶在了他的眼皮上,划出了一道血丝,距离他的眼球是这么接近。
我呢喃道:「当年你就是这样威胁那个女人的吧?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你感觉怎么样?」
朱程亨吓得瑟瑟发抖,嘴里啊啊叫着,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注射器里还有些不明液体,我直接按下注射,那液体喷涌出来,洒在了他的眼睛上。
- 慕倾雪(恩爱一百分:穆少的小娇妻)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慕倾雪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 2024-11-22
- 秦书琪苏云辰(苏云辰秦书琪)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秦书琪苏云辰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 2024-11-22
- (热推新书)《司绾绾穆宴辞》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千金盛宠穆少的掌心宠无弹窗全文阅读 2024-11-22
- 啾啾(啊这!疯批暴君读我心后被气哭)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啊这!疯批暴君读我心后被气哭小说全文无弹窗 2024-11-22
- 顾寒郑薇完整版(郑薇顾寒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郑薇顾寒最新章节 2024-11-22
- 复沦陷林冉傅行简正版美文欣赏林冉傅行简小说全文完整版免费阅读 2024-11-22
- 兰如裴今朝(隐神)全文免费阅读_隐神(兰如裴今朝)全文阅读 2024-11-22
- 顾清鸢萧云舟小说(渣男跪下,我嫁给你皇叔祖了)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渣男跪下,我嫁给你皇叔祖了)顾清鸢萧云舟最新章节列表 2024-11-22
- 萧持盈(和亲后,被阴暗坏批强取豪夺)未删减-萧持盈完结版阅读地址 2024-11-22
- 厉夜霆阮萌萌(主角是超雄老公,不许扯小娇妻的纸尿裤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厉夜霆阮萌萌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2024-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