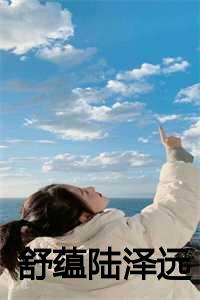- 作品分类
爱他第一秒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爱他第一秒)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爱他第一秒爱他第一秒)
54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3-11-10 19:07:57
编辑: 傅霁琛
我因为没有母亲被同龄孩子嘲笑,是他撸起袖子为我大打出手;我因为初潮惊恐万状,是他红着脸给我买来人生的第一包卫生巾。
我爱上他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并非情侣,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终将在一起。我自己亦深以为然,我参与他的人生长达十七年,他理应也爱我。
但是我在十七岁时失去了傅霁琛。
二
我第一次见李南舒,就已经预感到傅霁琛命里注定的辛德瑞拉出现。
那时候我的语文糟糕得一塌糊涂,父亲一个在教育局的女友辗转联系到了家境寒微、寻找兼职的师大高材生李南舒给我作家教。
她第一天来家里报道,穿浅蓝棉麻连衣裙,散着一头黑色长直发,怀抱着几本教材书,立在别墅前如瀑倾泻的黄木香下,好像天生就是女主角似的。
她给我试讲《氓》。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她的声音带着二十岁女孩子不应当有的哀婉和怅惘,为几行晦涩的白纸黑字平添凄凉。
等我下课的傅霁琛抱着手倚在门旁,就这样出了神。
十七岁的沈凝漪极其无理取闹。就像面对我父亲诸多的女友,我表达不满的方式是大呼小叫、摔打物件,等着父亲好声好气的哄我,好让她们看明白父亲对我这个丧母独女的偏疼,百试不爽。
所以我偏要傅霁琛当着李南舒的面给我系鞋带。
- (番外)+(全文)灵音裴玄:全文+后续(柔桑陌上吞声别)小说最新列表_灵音裴玄:全文+后续(柔桑陌上吞声别)全文阅读无弹窗灵音裴玄:全文+后续 2025-02-22
- 顾北辰桑苒苒结局+番外(顾北辰桑苒苒结局+番外)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顾北辰桑苒苒结局+番外(霸总爹地,妈咪又逃了)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霸总爹地,妈咪又逃了) 2025-02-22
- 傅京渊季染:结局+番外(季染傅京渊)全文季染傅京渊阅读无弹窗结局_季染傅京渊+结局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傅京渊季染:结局+番外) 2025-02-22
- (阮轻芷霍峥)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阮轻芷霍峥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 2025-02-22
- 季总别虐了,太太扔下离婚协议跑路了小说(桑榆晚季司宸)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总别虐了,太太扔下离婚协议跑路了全文免费完结版阅读(桑榆晚季司宸) 2025-02-22
- 重生之首长老公离婚指南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祁绍巍江云岚)_重生之首长老公离婚指南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祁绍巍江云岚) 2025-02-22
- 祁绍巍江云岚免费(重生之首长老公离婚指南)最新章节_祁绍巍江云岚免费全文阅读 2025-02-22
- 苏知谣顾廷烨(从爱上他的那刻起,我便被判了罪:结局+番外)全文最新免费阅读无弹窗_苏知谣顾廷烨精选章节小说阅读_笔趣阁(从爱上他的那刻起,我便被判了罪:结局+番外) 2025-02-22
- 《魏沐辰林诗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穿到七零我有两宝:一空间二萌宝无弹窗阅读 2025-02-22
- 你说得对,是我自找的(顾清欢陆霆骁)全文小说免费阅读_(顾清欢陆霆骁)你说得对,是我自找的最新章节列表 2025-02-22